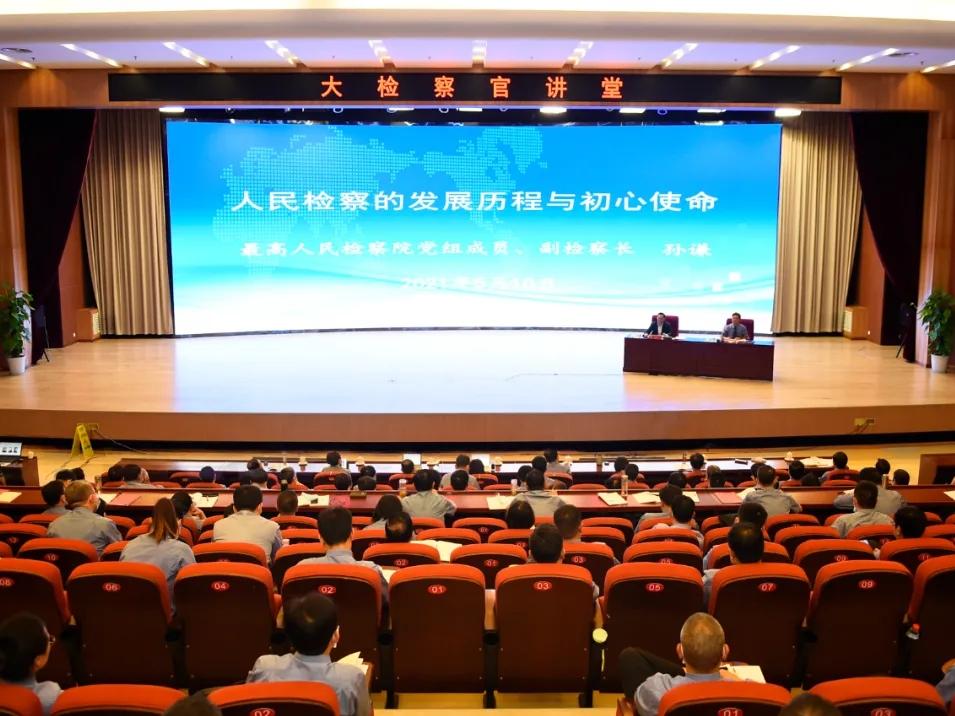2025年4月的某個傍晚,紅星醫院急診大廳里,李大姐攥著CT報告單的手在發抖。兒子術后并發癥的治療費像座大山壓得她喘不過氣,主治醫生辦公室前,她的聲音逐漸哽咽:“我們老百姓不懂醫,你們總得給個說法吧!”就在氣氛即將失控時,身著制服的法官古海尼沙快步走來,輕輕遞上一杯溫水:“阿姨,您看咱先到旁邊的法官工作室慢慢說,這里有醫院的調解專員,也有能聽懂病歷的律師,咱們一起把問題掰扯清楚。”

這溫馨的一幕,正是十三師中級人民法院與醫院共建共治的日常片段。當醫療糾紛的陰云籠罩在醫患之間,當法律的嚴肅與醫學的專業看似隔著難以逾越的溝壑,一場始于邊疆大地的社會治理創新,正讓法槌的鏗鏘與聽診器的溫暖產生奇妙共振,在守護生命尊嚴的戰場上,編織出一張剛柔并濟的解紛大網。
在矛盾的“病灶”上搭建共治平臺
回溯到一年前,十三師法院的立案大廳里,醫療糾紛案件數量正以每年25%的速度增長。“有的患者抱著X光片哭,有的家屬舉著錄音筆吵,醫生護士最怕收到法院傳票。”黨組成員、副院長游樂然回憶道。更棘手的是專業壁壘:法官對著復雜的病歷報告如讀天書,醫學會鑒定周期長達三個月,患者等不及結果就可能采取極端行為。
2024年春天,一場特殊的聯席會議在紅星醫院會議室召開。法院立案庭的數據分析圖與醫院質控科的糾紛統計表擺上桌面,兩組曲線在“術后溝通不足”“病歷書寫瑕疵”等節點高度重合。“與其等矛盾激化了打官司,不如在萌芽階段就介入!”中級人民法院院長蘆欽文的話點醒了所有人。于是,十三師法院聯動化解和預防醫療糾紛白皮書、以及首個設在醫院門診樓內的“醫法聯調法官工作室”誕生了,工作室的首場“實戰”就頗具挑戰。

78歲的張大爺在手術后感染,不幸離世。家屬認為是消毒不嚴格所致,帶著親友圍堵醫生辦公室。法官王圣佳帶著書記員匆匆趕來,首先做的不是講法律,而是請家屬選出代表,跟著醫院感控科主任走進消毒供應室,實地參觀手術器械的清洗、滅菌流程。”您看這臺德國進口的滅菌器,每鍋都會自動生成監測數據,這些電子記錄在系統里面都能查到。”當看到電腦里完整的消毒日志,家屬代表的語氣明顯緩和。隨后,法官又拿出《民法典》中關于醫療過錯推定的條款,結合鑒定專家的初步意見,幫雙方算出合理的賠償區間。經過6個小時的調解,當張大爺的兒子在調解協議上簽字時,突然握住王法官的手:“以前總覺得法官是坐堂問案的,沒想到你們會實地去了解醫院工作流程,會幫我們算清楚每一筆賬,以后有醫患解紛我們一定第一時間找法官!。”
這種“把法庭搬到醫院,將調解融入診療”的創新,讓糾紛化解周期從平均90天縮短到15天。2024年,法官調解室累計接待咨詢88余人次,成功化解糾紛46起,其中52%的案件在訴前就握手言和,并獲得全國平安醫院建設先進表彰。
從“案結事了”到“心平氣和”:解開醫患之間的“千千結”
2025年2月的一天,醫院的會議室里傳來陣陣掌聲。一場特殊的“普法課堂”正在進行,這種將普法課堂搬進醫院的做法,正在悄悄改變著醫患互動的生態,“醫法下午茶”準時開講。法官會帶著真實案例視頻而來,播放完患者大鬧診室的畫面后,突然暫停提問:“如果此時你是值班醫生,第一反應應該做什么?”急診科小劉舉手:“先按報警鈴?”法官搖搖頭:“正確的做法是立即請導醫引導其他患者撤離,然后傾聽患者需求,進行心理疏導。”這種場景化的教學,讓法律知識不再是冷冰冰的條文,而是變成了醫護人員手中的“防護盾”。
未來已來:當法治陽光照亮健康之路
站在2025年的春天回望,新星市的醫法共建共治已結出累累碩果:法院門口的醫療糾紛信訪量下降了30%,醫院的投訴率下降了45%,更重要的是,醫患之間的信任正在重建。在法官工作室的留言簿上,有患者寫道:“原來打官司不是吵架,是講道理的地方”;有醫生寫道:“知道了如何用法律保護自己,才能更安心地治病救人”。

而創新的腳步從未停歇。法院與醫院的會議室里,最新的合作方案已經出爐:在互聯網醫院開辟“法律問診”專欄,在社區打造“健康法治驛站”……暮色中的法官工作室的燈光依然亮著,年輕的法官助理正在整理當天的調解筆錄,醫院急診大廳里,醫護人員推著擔架匆匆而過,走廊的長椅上,患者家屬正在翻閱法院發放的《醫療糾紛化解手冊》。

遠處,法槌與聽診器的聲音交織成歌,那是法治與醫學共同譜寫的生命贊歌,是社會治理現代化進程中最動人的和弦。在這片充滿希望的土地上,當每個生命都能得到法律的守護,當每份醫者仁心都能獲得法治的庇佑,我們便真正走進了那個”糾紛可解、信任可建、未來可期”的美好時代。